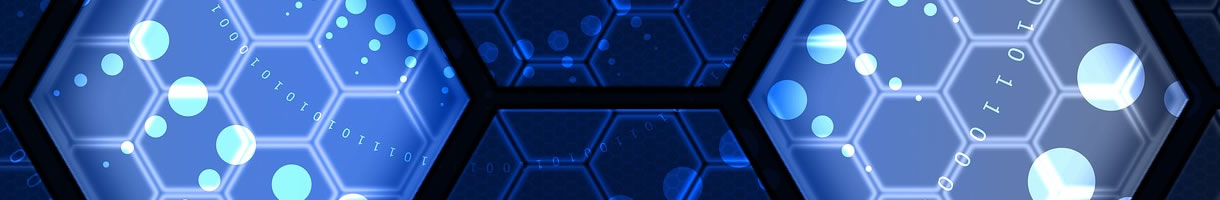89军军长刘伯龙太霸气,由于路上堵车,告成开枪打死修车军官!
你敢信?1949年,89军军长刘伯龙就因为车坏了,竟被当街一枪毙命修车的军官,这个候车军官作念梦皆莫原意想,他莫得死在敌东说念主之手,而是死在了我方东说念主手中。

刘伯龙,他不是匪贼,却比匪贼还横。他披着军装,却把军法当私刑,嘴上喊着“整肃规律”,暗自里干的全是撤消异己的勾当。最让东说念主寒心的是,通盘贵州官场,从省主席到县长,个个眼不雅鼻、鼻不雅心,妆聋做哑,仿佛惟有不看、不说,血就不会溅到我方身上。
那是在1949年6月,贵州乡间一条坑洼造反的公路上,尘土被炎风卷得漫天遨游。一辆军用卡车瞬息熄火,怎样也打不着火。司机是个保安团的少校,黄埔诞生,履历干净,为东说念主认知。那天他仅仅例行押运,车子中途抛锚,练习机械故障。他蹲在引擎盖前,满手油污,眉头紧锁,正谈判哪儿出了问题。
谁能意想,几分钟后,他会被一枪爆头,倒在我方修了一半的车轮旁?
开枪的,恰是刘伯龙。他带着几个相知,从辽远走来,脚步皆没停稳,手还是摸上了腰间的枪。没问一句“怎样回事”,没给一点解说的契机,“砰!”少校就地倒地,血从胸口涌出,染红了黄地皮。

周围几十号东说念主,有士兵、有路东说念主、有同寅,竣工僵在原地,像被施了定身法。没东说念主敢向前扶一把,没东说念主敢问一句“为什么”,致使连眼力皆不敢交织。不到五分钟,尸体透顶凉透。
你说乖谬不乖谬?一个没犯错、没叛变、致使灭顶过嘴的军官,就因为一辆坏掉的卡车,丢了人命。可对刘伯龙来说,这压根不是“错可以”的问题,在他眼里,你不属于他的圈子,便是挟制;你不百分百听他的话,便是隐患。
其实,这早不是他第一次入手了。
刘伯龙是蒋介石亲身空降到贵州的“钦差”,口头上是整顿所在武装,实则想把贵州酿成他一东说念主说了算的“清静王国”。他打心眼里瞧不起腹地保安团,合计这些东说念主“村炮”“懒散”“不专科”,恨不得全换掉。可告成铩羽容易激起兵变,于是他想了个“高效又省事”的方针:杀鸡儆猴。

三月,他的副官东说念主间挥发。那小伙子年青有为,暗里和刘伯龙的妹妹走得近了些,不外是泛泛往来,连手皆没牵过。可是这件事情在刘伯龙眼里,这便是“胡念念乱想”“觊觎家门清誉”,你说说,这还有端正?就这么,没审讯,没把柄,东说念主告成被拖走,尸骨无存。
五月,贴身文告也失散了。这位文告曾是战地记者,文笔敏感,来去机密文献多。刘伯龙怀疑他“可能”向外界浮现了什么,留意,是“可能”,不是“照实”。就凭这点造谣中伤的疑心,东说念主连夜被带走,从此音问全无。
六月,轮到了那位磨折的少校。口头意义是“延误军务”,实则因为他代表的是贵州腹地势力,不属于刘伯龙的嫡派班底。杀他,既能震慑保安团,又能向南京表诚意:“看,我在替党国清理派别!”
但信得过让东说念主心头发冷的,是十一月那起暗杀,前贵州省长卢焘,惨遭棘手。

卢焘是谁?他是护国斗殴的老英杰,早年随着蔡锷讨袁,为共和流过血、拼过命;自后主政贵州,爽朗自守,庶民称他“卢苍天”。1949年,眼看自若军势如破竹,世界大局已定,卢焘公开表态:闲适协作和平打法,幸免贵州再遭战火涂炭。这哪是反水?分明是救民于水火的大义之举!
可在刘伯龙眼里,这便是“通共”“叛国”。他容不下一个比我方更有威信、更能服众的东说念主存在。于是,在一个黯澹的夜深,老东说念主被强行拖披缁门。几天后,尸体被扔在城郊荒坡,身上布满弹孔,连件像样的寿衣皆莫得。
更朝笑的是,通盘贵州官场对此集体失声。省主席谷正伦,经验老、地位高,按理说能压住刘伯龙。可他怕啊!刘伯龙背后站着蒋介石,谁敢动他一根汗毛?谷正伦只可暗里叹语气,对心腹嘟囔一句:“作念事要讲法例,别闹太大。”这话听着像是告戒,实则是默认,默认暴行不绝献技。

镇宁县长更绝,传闻又有东说念主被枪毙,他眼皮皆不抬,告成甩锅:“军方里面事务,所在政府无权干预。”好一个“无权干预”!明明是光天化日下的谋杀,却拿轨制当遮羞布。说白了,公共皆抱着“惟有刀不砍我头上,我就当没看见”的心态,任由懦弱在街头彭胀。
而刘伯龙的辖下呢?活得比囚徒还面不改色。他的卫队开着玄色轿车,在贵阳三街六市往来转悠,士兵手经久按在枪柄上,眼力冷得像腊月的井水。他们不是保家卫国的军东说念主,而是私东说念主打手。谁如果多问一句“副官去哪儿了?”,第二天可能就“病假”了,再也没总结。想写信举报?信寄不出去;想去上告?东说念主先被关进黑牢。通盘系统,成了他一个东说念主的恐怖戏院。

1949年下半年,国民党政权早已摇摇欲坠,里面出现很大问题,极不慎重。自若军度过长江,西南各省纷繁易帜。刘伯龙心里门儿清:我方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越是阁下崩溃,他越要攥紧临了极少时期,把通盘“不慎重身分”,有威信的、有办法的、有民气的,系数取销干净。在他误会的逻辑里,惟有把这些东说念主皆干掉,我方就能在乱局中多撑几天,说不定还能带着相知百死一世。
但他忘了最重要的极少:暴力能吓住东说念主,却留不住心。当他亲手砍断副官(亲情)、文告(忠诚)、少校(步骤)、卢焘(民气)这些提拔权利的提拔时,他我方也站在了万丈绝壁边上。没东说念主替他传消息,没东说念主帮他组织防地,连最亲近的东说念主皆隐藏得鸦雀无声。到临了,他身边只剩下一帮吓破胆的伴随,和沾满血的枪。
几把
历史从不骗东说念主:靠屠刀维系的权利,注定夭折。几个月后,贵州自若,刘伯龙仓皇出逃,最终被东说念主民审判、计帐。而那些被他杀害的东说念主,卢焘、少校、文告、副官,他们的名字大致不再天天被东说念主拿起,但他们的故事,却在贵州的茶楼、田埂、老屋檐下世代相传。老庶民心里有杆秤:谁真心为这片地皮流过汗、流过血,谁仅仅把这里当跳板、当猎场,一清二楚。

举座看来,刘伯龙打着“规律”的幌子,干的是摒除异己的脏活;口口声声“效忠党国”,实则只想割据自雄、独霸大权。这种东说念主,别说当将军,连作念东说念主皆区别格,您合计呢?
信得过的军东说念主,该像卢焘那样,国度危难时挺身而出,时期改造时顾全大局;信得过的规律,应建树在轨制、口头与公说念之上,而不是某个东说念主的一念之怒、一时之快。刘伯龙式的“强东说念主逻辑”,看似风风火火,实则纸糊的老虎,风一吹就倒。因为他靠的不是东说念主心,而是懦弱;而懦弱,从来留不住东说念主,只会加快坍塌。